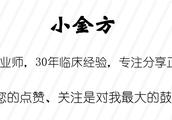打开资讯app,每天我都会收到各种令人振奋的最新医学研究成果的报道。我的即时通讯工具上,也不断的有人向我推送他们看到的各种医疗资讯。
时间长了,我对这些资讯感到疲劳了。抗癌十多年,麻木了,现在我多数时候连打开链接的欲望都没有。
同样令我感到疲劳的是,越治越多的癌症病人。病人无穷无尽,每天的工作都好像无尽头。
我现在不得不婉拒掉大部分患者的求诊,推掉很多咨询,因为我的精力和时间不够用。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病人?医疗给病人带来了多大帮助?这是我经常在思考的问题。
2012年,一个老大夫建议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癌症这类顽疾的致病原因上,从源头上杜绝癌症的发生。他认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更有意义,病人是根本治不完的。
他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一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在来势凶猛的癌症浪潮中,我们就像是狂风巨浪中的一叶轻舟,飘摇不已,所能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
我想几乎每个医生应该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就在我写此文的这一天,兰州某军区医院肿瘤科主任,上海某知名医院的某位肿瘤科的西医专家,和北京某肿瘤医院的某位专家,都推荐去找他的患者来找我看病。
与此同时,我也在推荐来找我的患者,去某某医院寻找其他医生的帮助,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也就在这一天,一个在日本和美国治疗无效,在国内屡经各个知名医院里的知名专家治疗无效的乳腺癌患者自己找上门来,找我治病。
这是我们医生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片段。其实每天在世界各地,我以及那些把病人推荐到我这里来,还有我推荐病人去寻找的另一些医生们,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我们很无奈的面对一群群的求助者,有时我们对自己的治疗效果很没信心,只好极力说服患者去别的地方接受其他的治疗方案,分担压在我们心头和肩上的压力。
没有多少人在自己的同类面临死亡的威胁时仍然能够无动于衷,强烈的求生欲望使得病人和病人家属对医生有过高的期望,这期望压得医生透不过气,所以我们会以各种理由推掉很多的求助者。
不得不承认,有时我们把患者互相介绍来介绍去,是我们自己在逃避现实。固然,我们心中确实对其他治疗方案存在一线希望,希望患者在其他医生那里获得更好的治疗,但是更多的可能只是我们自己不愿意面临患者即将临终的残酷现实。
我的生物钟有异于一般人,一般来说,我入睡很早,半夜三点多钟我会醒来,此后就会在阅读各种医学文献中度过,一直到天亮。这个时间段万籁俱寂,很适合安静的思考。
我常常会在早起后,回过头去想我治疗的患者们,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长眠地底,我常常会反思医疗给他们带来的究竟是帮助还是害处。
我们医生在他们身上动刀子,割下一块又一块的组织,我们用各种设备和药物去治疗他们,短暂的遏制他们病情进展的同时,也给他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带来很大的伤害和负担。患者耗尽钱财的同时,精神和肉体都疲惫不堪,不久还不得不面临病情复发的残酷现实。
我经常遇到对医生很厌恶的晚期癌症患者和患属,我对他们的心情很理解,肿瘤科医生自身的抑郁情绪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
作为医生,患者和患者家属曾经一度对我们有很高的期望和信任,但是最终我们给他们带来的是失落和绝望,有此遭遇,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厌恶和失落情绪不难理解。
曾经有个患者的女儿,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找了一个西医肿瘤外科专家后再来找我,她跟我说,她找的这个专家对她说,他当医生越久,就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治病了。
这位外科大夫的话于我心有戚戚焉。有时我也会感到大脑一片空白,面对一个病情复杂的病人,不知所措。
我们在上一个病人身上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治疗效果的方案,用到下一个病人的身上时,很有可能会加速下一个病人的死亡。而不被我们看好的治疗方案,却在有些病人身上创造了奇迹。
最终我们不得不怀疑,我们所学的医学理论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而我们所谓的经验,又有多少是真的有价值的呢?
我曾经用中医给一个西医老专家治疗她的淋巴瘤,开药时我内心惴惴不安,我对患者说:“李大夫,我觉得自己像是在做人体实验似的。”
这位临床了一辈子的老大夫说,她做了一辈子的临床实验,医生的工作,说到底就是在做临床试验,如果没有敢于做这种临床试验的勇气,就当不了医生。所以她鼓励我把她当临床试验的小白兔。
医生的工作在本质上,和赌徒也没什么区别,只有掀开盖子的那一刻,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输了还是赢了。

所以我总是要求我的患者在治疗期间,一定要定期检查,及时告诉我结果,评估疗效,如果疗效不佳的话,要尽快另寻高明,以免耽误他们的治疗。
但我也越来越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另一种逃避。今天我接诊的一个肺癌患者,经我治疗了一个多月无效,我希望她的家人考虑化学治疗方案。
实际上患者已经尝试了好几年的化学治疗方案。找到我,只不过是不再希望重复旧路而已,扪心自问,当我推辞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我或许也是在逃避现实,是我自己内心里,不愿意面临最后的失败而已。
当我向那位到过日本和美国治疗过的患者推荐射波刀来解决她肝脏的弥漫性的转移病灶时,患者自己做了另一种选择。
她已经对西医感到绝望,不再愿意做任何西医治疗,她希望我能够用纯中医治疗来维持她的生活质量,她对死亡不再畏惧,她只不过希望死得不那么痛苦而已。
而这位患者的丈夫,正在北京寻找他们曾经就诊过的,中国某位最有名的乳腺癌西医专家。笃信现代医学的他,尽管已经碰壁,还是希望妻子继续接受令她感到痛苦和绝望的西医规范治疗。
但是这位西医专家,其实也已经无计可施,我知道他和我一样,面对这样的局面,内心中极为苦恼。
究竟是患者自己的选择对?还是我给患者的建议对?抑或是患者丈夫的坚持对?我难以评判。
我对医疗的困惑和畏惧心理,和对接诊重病患者的畏惧心理,与日俱增。下午的时候,一个重病的肝癌病人的女儿,主动给我发了个红包,希望我能够就其母亲的病情给她一些建议,我给她提供了一些职业化的建议后,拒收她的红包。
我一点都不清高,也不高风亮节,我不是不需要钱,也不是不爱钱,而是这钱我不能要也不敢要,因为面临如此危重的一个病人,我得掂量着,自己远程协助,究竟是在害她还是在帮她。
傍晚时,另一个患者家属邀请我到外地出诊,去治疗他家的亲人。他问我:“你能否告诉我,你能治疗出什么效果?”我据实告诉她,我也不知道,这样的回复对患者家人来说是一个打击。
最近的两三个月,我已经婉拒了很多邀请我出诊的请求,只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真的无法帮这些危重到不能到北京来就诊的患者解决什么问题。
我见过的治疗得最好的一些癌症患者中,颇有几个不是医生治的,而是他们自己找了些偏方在吃。
我曾经在山东蓬莱追访过一个挖苦参根泡水喝的胃癌患者的家人。在患者的家乡,患属带我找到了他们自己不认识的那味草药,我唯一比他们强点的就是能够辨认出这味药材并告诉他们这味药材的学名。

这个患者当初在医院进行剖腹探查手术时,医生看到患者整个腹部长满了肿瘤后,决定不予切除,将患者腹腔缝合后,让患者回家。按照常规,这是活不过半年的。
患者回家后用这味草药苦参泡水喝后,再经五年半才死亡,死之前又去医院做了一次手术,腹腔内的肿瘤已经消失殆尽,但是肝脏长满了转移瘤,患者因此而去世。
另一个卵巢癌患者腹水后,也是经他们本地的草头郎中的指点,挖小蓟根炖排骨吃,不到一周就把腹水全消掉了。我的作用同样只是帮助他们辨认出他们所挖的草药是什么,告诉他们学名。

民间有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父。又有俗话说,海上方气死名医。我得承认,换了我去治疗,我很难取得比这更好的疗效。
非但我,放眼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体系内,无论哪个医生,无论他的学位或职称是什么,都未必能取得比这更好的疗效。
我们孜孜不倦的探索,我们认为我们的医学在进步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实际上无数的医务工作者,可能正在探索的是,将患者带入疲惫不堪的境地的弯路。
很多患者靠着运动来消耗自己身体内过剩的糖类和脂肪,靠着采取更自律的生活方式,靠着适度的缓解症状,进行少量的功能性治疗,所取得的生存质量和生存期,可能比我们让患者倾家荡产的治疗所得到的结果更好。
当全世界的医疗体系,都在重视经济效益的时候,我们的医疗不可避免的被拖进了可能与真实的事实相冲突的境地之中。
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过度的治疗,和对病人过度的呵护,正在把病人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原始的本能力量弱化掉,带病人走进了一条深不见底的死胡同,同时也把医生自己带进了深渊。
我们嘲笑原始社会的初民靠巫术治病,但是在绝症面前,我们似乎不比那些巫师们更有能力。
我们用医学术语编织了一整套话语体系,社会大众在这套话语体系中被深深恐吓,他们迷信得了病一定要采取某种业已形成固定习惯的治疗方案来治疗。
我们只要想着百年前的医生们和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百年前的患者们和我们今天的患者遭遇的心境差不多,而百年前医疗方案和现在的医疗方案截然不同,百年后我们的医疗方案和今天的医疗方案同样会截然不同时,我们就不能不感到吃惊,羊群效应在医疗问题上是多么可怕的存在。
我们人类的一个很顽固的缺点就是对自己过度的自信,很少有人想过,我们的所谓的自信不过是来自于我们所受的各种教育形成的思维惯性,说到底并不是我们有多自信,而只是我们对某些在社会上业已成型的思维结果的迷信。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在继续前行前,安静下来想一想,或许不是什么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