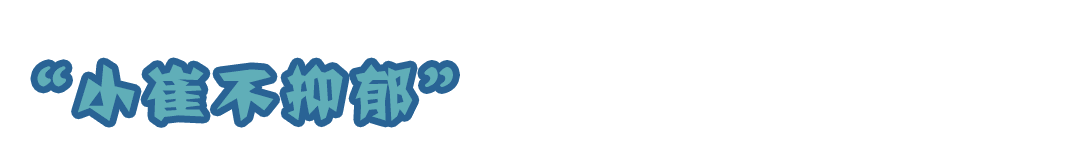

心灵受伤了需要医疗,就像身体生病了需要看病一样。但医疗心灵的医生,与治疗身体疾病的医生又有很大不同。
我国的职业分类中其实是没有心理医生这个称号,普通大众喜欢把针对心理工作的具有医师资格的医生称为心理医生,其实是精神科医生。而心理治疗师往往不具备行医资格,是不能被称为心理医生的。
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医生,可以根据病情、喜好来选择为患者用哪些药物;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和训练背景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
这些很重要,但对于每个寻求帮助的不同的个体来说,又不那么重要。
仁萱发给我一张孕味十足的照片,她说下个月就是预产期了,目前一切顺利,谢谢我在她困难的时候曾经帮助过她。
我记得她,一个曾经遭受过情绪困扰,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女孩。最后一次就诊时她带来一副画,结束时对我说:“我把这幅画寄存在你这里吧,我想让那些美好和不美好的回忆停留在此刻。”
我说可以,你想取回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吧。我知道她应该不会再来,此刻的停留是另一段美好的开始。
一位学员和我聊起她最近接受心理督导的感受。这是一次公开的案例教学督导,她很紧张,也很忐忑,但是又不想错过这次难得的专业提升机会。
但是,心理督导过程却让她很是失望,督导师当着上百人的面说“你的咨询只会让来访者变的更糟,她很不幸遇见了你这样一个心理咨询师。”整个督导过程充满了批评、指责和否定,督导结束后,她唯一的收获就是:我真没用!
我推荐一位朋友去精神卫生中心评估,前台的护士问她:谁是病人?朋友说,是自己。护士接着问:监护人来了吗?
朋友很无奈,我已经是成年人,不需要监护人。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身份证拿出来登记吧!尚未就诊和评估,她就已经被贴上了需要监护的精神病人的标签。
上周一位患者辗转来到我的门诊,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服用了6种药物,包括2种抗精神病药,1种抗抑郁药,1种对抗不良反应的药物,1种帮助睡眠的药物,还有一个中成药。
她的幻觉和妄想的确没有了,但是整个人显得木讷、呆板、没有精神,整天在家里要么吃,要么睡,体重增加了30斤。她说,我现在就是个废人,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我问她,病人和废人之间你更愿意做哪一个呢?她说,我宁愿生病。

我曾经分享过一系列在德国精神卫生机构参观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有同行说,我一天看病人几百个,你一天才看几个?这种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不适合中国。
看病人多似乎成了我们无法开展高质量工作的重要因素,但这不是我们不思进取的理由,更不是伤害患者的借口。
上课的时候,我喜欢给学生说,你面前的患者将来恢复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你和TA对待疾病的态度,确切地说,是取决于你和TA 对待疾病背后那个人的态度。
今天我值夜班,接到病区值班护士的电话,有个病人病情反复需要处理。我打开封闭病房的铁门,匆忙地走向病房。狭窄地走道里坐满了正在用晚餐的患者,当我处理完病人返回时,过道里的病人大都已经吃完。
只有一个桌子上的病人还在吃饭,我走近时发现是一位看起来20多岁模样的男病人,正在给一位年龄稍长的病友喂饭。
我停下脚步问他:“为什么你给他喂饭呢?”他腼腆地笑了一下;“我看他吃的很慢,很费力,我就帮帮他。”我注意到,年长病人的双手会不自主的抖动,行动也较为迟缓。我说:“谢谢你!”
我们每天遇见形形色色的求助者,识别各种各样的症状,精确的诊断、开药,试图消灭这些疾病。
我们满眼都是病,都是缺陷,想尽一切办法来驱走病魔,结果疾病往往就这样赖着不走了,永远和TA待在一起,TA成了一个永久的病人。“病”成了一个舒适带,我们舍不得也不敢走出来。
做医生的初期,我非常想把一个病人治好,却越来越发现在疾病面前我们是渺小且无助的。我有时候比病人还渴望改变,恐惧不变。
一位从高中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男孩,服用抗精神病药物长达6年,期间停过几次药,结果症状都反复。他学的是轮船驾驶,大学毕业后不得已要远航,医院配的药远不够一次航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航行回来后,他的病好了,并且工作出色,职位快速晋升,奇妙的是他的妈妈病了,被诊断为抑郁症。这是我大约7年前看的一个病人,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思索,这个所谓的精神分裂症对他和家人有什么意义吗?病竟然会转移?
当我换一种态度对待疾病和病人时,TA(病人)和TA(症状)竟然也会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

著名的策略派心理学家海利认为“症状是一种适应于当前社会情境的策略,当所有的其他策略失败时就采取这种策略以控制关系。”
如果症状是一种策略,可不可以和TA一起深入探讨,采用不生病的方式来解决困境?如果身上的资源乏善可陈,那就把疾病当做一种解决问题的资源吧。
美丽心灵中的纳什,最终与症状达成了和解,疾病永远都没有消失,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幻觉和妄想不再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再是他需要来解决的问题。
仁萱逐渐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抑郁有时候还在,曾经的苦难和不幸偶尔还会跑出来,但是当她送走那幅画时,和过去的纠缠说了再见,她看见的是可以肆意创造的未来。
我对那个在督导中倍感挫败的学员说,我相信你在以后的咨询中对批评、指责和否定的敏锐度会提高,这就避免了你无意中对来访者采取类似的方式,这是你此次督导最大的收获。
我不知道那位帮助病友吃饭的病人的病情和诊断,但是在那个时刻,我没有发现他的病,却看见了身上的光辉。

我国的精神科医生只有27733人,而精神障碍患者有1亿多人,平均每人要应对几千人,还不包括那些没有达到临床诊断也需要心理帮助的人。
普通的精神科门诊中,一天看上百个病人是常态,如何在这种繁重的工作中融入一点点的改变,来更好的理解患者与TA合作呢?
不批评、不指责、不强求
中立的对待患者和症状,没有一个人是主观上想生病的,哪怕这个病是有意义的,也是TA的无奈之举。
最容易让医生感到挫败和愤怒的是,我们反复叮嘱TA不要停药,TA还是把药停了,结果复发了。
此时我们要看到停药背后的力量:TA想尝试通过自己控制病情,或者TA病情恢复的不错……起码,TA获得了一个经验-我还是要服药的!
如果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强制治疗的程度,我一般不会强求患者服药,肯定TA不想服药背后的动机,告诉TA药物的获益和副反应,或者试验性的治疗和不治疗。

充分讨论症状背后的心理冲突
虽然精神疾病有很确切的生物学因素,但是几乎每个患者症状背后都有自己的辛酸史。或许那才是TA真的病,症状只是一个标签化的征象而已。
建构症状的功能和意义
很少有病人24小时都处在症状之中,对例外保持充分的敏锐度,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一定不在疾病里,在TA的健康资源里。
每次花一点时间听听TA谈论症状以外的东西,当你与TA无病的生命旅程建立深度联结时,症状会奇妙的减弱或消失。
症状很痛苦,但也是有功能的,看见功能才会放弃抵抗,同时减弱症状对自己的控制。精神病人的标签才会被慢慢撕下。
关注病人的系统
每个人都处在系统之中,尤其是家庭系统。患者在医院病情稳定,家属探视或出院后不久,病情往往会反复。与家属和身边重要的人合作,探索家庭系统的影响和资源,是患者恢复的重要因素。
尊重患者的不变
这点比较难,尊重不变不等于不干预,不等于不给建议,是一种理解和共情的较高境界。TA不变,一定有TA的原因和道理!

传统精神病学的诊断、评估和治疗一定是需要的,在传统流程中加入这些对待疾病和病人的态度,可以让双方的合作关系变的更立体和丰满。
重要的是,加入这些元素进去,花不了我们多长时间!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心理科陈博士
(ID:develop0909)
作者 / 陈发展
(小崔不抑郁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