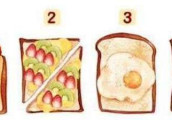主诉:心慌1月余。
病史:患者1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心慌,心悸,偶见下午疲乏、恶寒,性急易怒,口唇偏紫,无乏力气短,无胸闷胸痛等表现,纳可,寐欠安,二便调。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而涩。既往体健,半年前体检,心电图呈窦性心律失常,未予诊治。即刻血压:146/95mmHg;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非勺形改变,晨峰血压明显升高,全天血压平均值125/80mmHg,白日血压平均值130/90mmHg,夜间血压平均值110/67mmHg。

西医诊断:窦性心律不齐,高血压;中医诊断:心悸。辨证:气阴两虚,心阳不足。治法:益气养阴,通阳复脉。
处方:炙甘草汤加味。炙甘草15克,党参10克,生地25克,桂枝10克,阿胶10克(烊化),麦冬10克,当归10克,麻子仁15克,大枣5枚,生姜3片,夜交藤20克,酸枣仁30克,生牡蛎30克(先煎),生龙骨30克(先煎),黄酒为引。7剂,水煎服,日1剂,分早晚温服。
二诊(2015年9月24日):服药7剂后,患者诉心慌、心悸依旧,无明显变化,下午疲乏、恶寒稍有好转,夜寐欠安,仍性急易怒,大便不成形,2次/日,小便可,余无明显不适。舌质红,苔薄黄,脉弦细。即刻血压:139/90mmHg。处方在原基础上改生地50克,黄酒为引。14剂,水煎服,日1剂,分早晚温服。
三诊(2015年10月8日):服药后,患者诉心慌、心悸明显减轻,已无疲乏感,余无任何不适。即刻血压:135/84mmHg,舌脉如前,仍宗前法出入。前方去夜交藤,继予14剂。
四诊(2015年10月22日):患者已无任何不适,即刻血压:138/86mmHg。复查心电图:未见明显异常。后随访3个月患者未出现心慌、心悸等临床表现,告愈。
按:初诊不效,二诊后显效为何?笔者结合此案例谈谈对炙甘草汤的认识。

炙甘草汤出自《伤寒论》原文177条:“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主之。”此文概括了炙甘草汤主治证的病因、病机及主治证的特征。条文中的“伤寒”二字,从现存较早的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和明·赵开美影宋刻本《伤寒论》,至现行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伤寒论释义》和《伤寒论选读》,多认为其为太阳表证。而在太阳病篇里又分别论述了中风、伤寒、风温等病证,可见太阳病篇的伤寒应为狭义的伤寒,由此可推断,导致“脉结代,心动悸”的病因为外感风寒之邪,而该病除了具有“脉结代,心动悸”外,还应同时或初起具备太阳病提纲证。《医宗金鉴》中说:“炙甘草汤,仲景伤寒门,治邪少虚多,脉结代圣方也。”所以,笔者认为炙甘草汤主治证应为表里同病,虚实夹杂证,但以里、虚证为病证的主要方面,故原文中只列出“脉结代,心动悸”为主的特征性表现。我们在临床上应用此方,也当如仲景所言,“伤寒”二字,绝非可有可无之笔,抓其主症,据一点而攻其全局。
关于方中的君药和药物配伍关系,笔者以为初诊不效,而二诊改其一味,则动其全关,收效显著,正是仲景用药精当所在,后世所当遵仿之处。所谓君药,《素问·至真要大论》云:“主病谓之君,佐君为之臣,应臣为之使。”其后张元素言:“力大者为君。”元代李东垣《脾胃论》对君药论述则更为详尽,其曰:“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佐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由此可见,君药即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方剂组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君药药味较少,而且不论何药作为君药,其用量比作为臣、佐使药应用时要大。
观之炙甘草汤,仲景原方用生地黄一斤、炙甘草四两、桂枝三两,此则暗示病由外感而起,外邪犯表,首犯太阳,导致太阳生理功能异常,发为太阳病。其后出现心动悸,脉结代则说明表邪尚未解除,病已由表入里,由太阳转入少阴,少阴为心肾两脏,若不传足少阴肾,则传手少阴心。若少阴内虚,脉道失充,气血运行艰涩,则极易出现少阴心悸之证。所以,治之要大力滋阴补血,以图充脉养心,俾使心得养,阳得续,脉道利,正气来复则诸症可愈。
本方唯有生地黄具统解诸症之功效。生地黄具有滋阴补血、充脉养心的功效,是针对心阴血不足而用。然生地甘寒,入肾经,能滋阴补肾、清热凉血、生津止渴,味甘配炙甘草缓肝之急。

肝木之急,除甘以缓之法除外,尚有滋水涵木一途可循。肝肾乃是子母之脏,有肝肾同源、乙癸同源之说。故重用生地黄滋肾水以涵肝木、息肝风、降肝经浮游之火,此亦其功用也。《神农本草经》另记载其:“主寒热积聚,逐血痹。”说明生地能疏通痹结之血脉。肝藏血,心主血脉,生地一味药而兼具滋阴补肾、柔肝缓肝、养心复脉之功。因此,张仲景的炙甘草汤方重用生地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故而考虑炙甘草汤君药乃为生地黄,而非世医常谓之炙甘草。
对于其药量,首诊生地用为25克,炙甘草用为15克,7剂服尽而未显寸功。二诊时生地加至50克而收显效,则显示对于炙甘草汤而言,巧妙掌握生地和炙甘草的比例,在治疗心悸中的重要作用。此中玄妙,值得我辈学子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