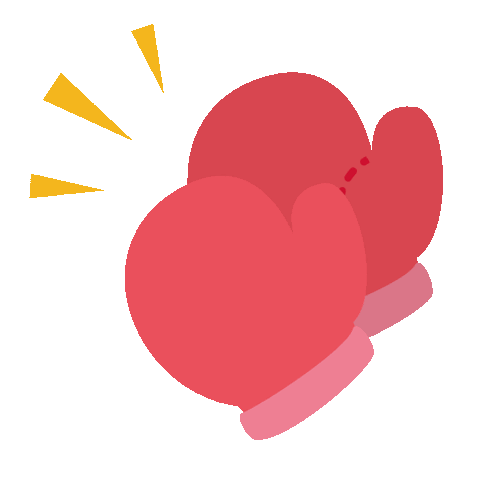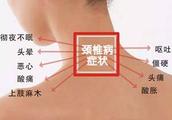“妈,我恨你!”
母亲与女儿的关系天然复杂。
她们曾经在一个身体里共生,却以女儿入侵母亲身体领地为开始。
她们通过脐带血脉相连,但如果母亲的脐带缠绕过紧,女儿就会窒息。
当女儿摆脱母亲的脐带来到世界,她的体内还流动着母亲的自我。
[秋日奏鸣曲]的母女
因此,女儿与母亲的较劲注定旷日持久,它可能是外露的,但更多时候是隐秘的。
隐秘不代表不激烈。
特别是女儿萌发了自我意识之后,外界的一丁点变化,都会在母女之间搅动起风暴。
SARS,癌症,逆文化冲击,电影[美国女孩]设定了一个相当兵荒马乱的青春期。
故事的主角,一对母女,被安置在拥挤的两居室。
两居室内还有爸爸和妹妹,但他们只是作为母女关系的旁观者和催化剂存在。
不完美的母亲和不完美的女儿始终在台前,贡献了一场以爱为武器的隐秘战争。
停战协议也是爱,双双负伤后她们明白:
爱是双刃的武器,当你刺痛对方,同时也刺痛了自己。
恨从何来
妈妈患了癌症,芳仪被老师用教鞭狠狠打了手。
在女儿芳仪看来,这是一条顺理成章的因果链。
小学毕业移居美国,好不容易被妈妈逼着每天背20个英文单词,成为讲一口流利英语的“美国人”。
如今却为了给妈妈治病回国,从全A资优生变成班级倒数,被老师和全班同学嘲笑是“美国人”。
这一来一回,芳仪都是被动的。
去美国更多是妈妈的意愿,她想借助女儿,去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美国梦。
也许还想找个正当的借口,逃离自己的丈夫。
这是儿科医生阿尔多•纳乌里的观察:
“母亲越是与女儿紧密相连,越是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完美化身,成为自己的克隆人。”
那时的芳仪,自然地接受了最亲密的母亲转移到她身上的自我。
但随着年纪渐长,她开始质疑: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想当美国人呢?”
这次从美国回来,她更不愿意买账了,动不动就嚷嚷着要回美国。
不是因为美国有多好,而是她不需要再为了适应迥异的文化换层皮,似乎也不需要面对像现在这样焦虑的妈妈。
患了乳腺癌的妈妈的焦虑,是她所不能承受的。
作为家里离死亡最近的人,妈妈无法对未来做出乐观的预期,甚至偷偷看起了临终关怀的小册子。
她一面焦虑于生命的流逝,一面惯性地将自我奉献给家庭。
在医院做完化疗,她忍着不适,照样买菜做饭、清洁房屋。
主外的丈夫做不好这些,他不知道女儿最讨厌吃番茄酱,不知道家里的鸡蛋哪天吃完,一回家不洗澡就往床上倒。
繁重的家务在化疗后的身体上变成了一座山,在精神上同样如此。
坐在化妆台捋下来一撮头发后,她跟要出差的丈夫讲:
“是啊,在这里是等死。”
每每听到这种话,丈夫会选择逃避她的情绪,背过身抽烟,抽了一根又一根。
为了维持情感需求,她只有靠女儿了。
有时候,她会通过母亲的权力,向女儿施加控制。
比如,给女儿榨混合果汁,端给她们喝。
芳仪觉得难喝拒绝,她就会威胁:
“你长大之后,得癌症就不要怪我。”
有时候,她用隐晦的语言渴望女儿的宽慰。
芳仪给她擦身子,问她病好了能不能回美国。
“说这个有什么用,反正妈妈可能也活不久。”
但女儿并没有分担妈妈的死亡焦虑,她本能地想逃避,同时为自己的逃避焦虑。
芳仪陷入了心理学所讲的“情绪的洞”,作为女儿她天然吸收妈妈的情绪,又因为产生了自我意识,隐隐约约分辨出这个情绪不是自己的。
“离开这个洞,似乎背叛母亲,让母亲一个人孤单待在洞里。这样的矛盾挣扎,感受到被绑住而不自由,渐渐掺杂不忍心的担心害怕,以及脱离不了的愤怒与无力感,纠缠而进退两难。”
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芳仪选择怨恨妈妈。
她在演讲稿里写: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
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
她开始站到爸爸的那一边,一起指责妈妈“为什么不能勇敢”。
为自己的焦虑找到替罪羊,她感觉好受一些。
而夹在中间的爸爸,让母女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他一面听老婆的话带女儿买书桌,一面听女儿的话把书桌换成梳妆台。
矛盾像接抛球,实际落在母女之间。
“功课这么差,还给她买梳妆台。”
“那是我挑的,不关爸爸的事。”
就这样,妈妈被最亲密的女儿疏远了,而女儿也越来越不满妈妈的权力控制。
母女在情绪的洞中互相争夺自我,越陷越深。
恨是爱本身
相较来说,女儿消耗的情绪更多。
妈妈有怎么也逃脱不掉的母职之爱,女儿却在恨意和愧疚之间左右摇摆。
芳仪表达恨意的方式,无非是故意唱反调,用妈妈的爱来惩罚妈妈。
阿德里安城·里奇在《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一书中,把这种做法归因于“惧母症”。
女儿认为母亲是“不自由的受害者和殉道者”,担心自己“除继承母亲的个性特征之外还注定要继承母亲的‘身份地位’”。
有什么比否定母职本身更好的惩罚方式呢?
所以芳仪在争吵时,会回怼妈妈“不用担心,我不会生小孩”,言外之意是“生小孩才会得癌症”。
从网吧晚归,她无视妈妈的关心,把饭盒一丢直接摔门进房间。
第二天去学校,妈妈带的饭她一口不动,连饭盒一起原样带回家。
她觉得这样能伤到妈妈的心,也确实如此。
妈妈主动服软,带她和妹妹去西餐厅吃冰淇淋。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想了好久,打开灯找出了和妈妈的合照。
照片记录了她们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她们还在美国,妈妈带芳仪骑马,而骑马后来成为了芳仪最大的爱好。
“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照片上妈妈的人像被折去,芳仪曾经用这样的方式悄悄表达着恨意。
那天晚上,她看着照片上的折痕,心里翻江倒海。
恨意来源于爱,可以在一念之间生起,也可以在一念之间消逝。
但在药到根除之前,恨意也是反复的,非得往最痛的地方扎下去不可。
在妈妈为妹妹的肺炎焦头烂额,不让芳仪参加演讲比赛后,母女俩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吵。
芳仪:“我好好上学你又不爽。你什么时候在意过我想要什么,你就只会说我害你得癌症。”
妈妈:“我不是为了你们待在美国的话,我哪会得癌症。”
芳仪:“不要再把你的问题都怪在别人头上。”
妈妈:“你觉得我有选择吗?”
芳仪:“你总是能选择。”
越是亲密,越知道怎样刺痛对方。
妈妈跑去芳仪的房间,撕毁了她墙上印有马的海报。
两个人互相推搡起来。
妈妈:“我不想活了,你把我杀死算了。”
芳仪:“你想死就死啊,反正你又没有要好好活着。”
争吵以芳仪离家出走,而后被警察送回作结。
她在无意间看到妈妈崩溃的样子——
晾晒衣服时,躲在床单后面大哭。
此刻的她,悔恨的心情达到了顶点。
她总觉得妈妈可以做得更好,但就像她唯一的好朋友说的“这如果已经是她的最好了呢”。
妈妈发现女儿在每一页书角画的马,懂得她想要的自由
她不是想不通这个道理,只是惯于逃避罢了。
在看到了对方最痛的模样后,母女二人开始和解:
从女儿接受母亲是普通人开始,从母亲接受女儿是独立的个体开始。
她们早已达成了最亲密的默契,是那种独属于母女的细碎的、小小的默契。
芳仪请妈妈帮她掏耳朵,就这样一搭一搭地聊起来。
“妈妈,你还记得我以前问你,你下辈子想当什么动物吗?”
“你说你想当马。”
“那你还记得你回答什么吗?”
“不记得了。”
“你说你下辈子想当男生。”
“妈妈,你不要死好不好?”
“妈妈很爱你,你知道吗,好爱好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