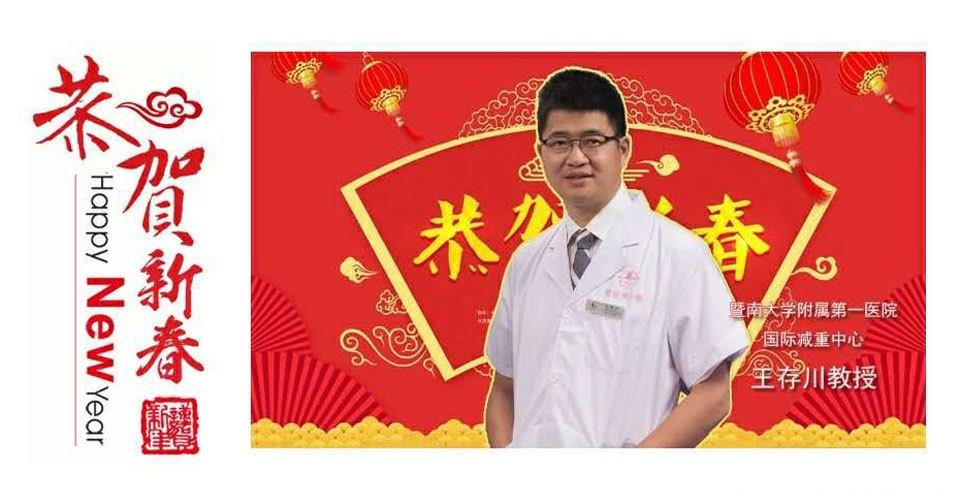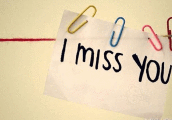性与反浪漫主义
性与浪漫有不解之缘。性本身具有一种美化、理想化的力量,这至少是人们共通的青春期经验。仿佛作为感恩,人们又反转过来把性美化和理想化。一切浪漫主义者都是性爱的讴歌者,或者——诅咒者,倘若他们觉得自己被性的魔力伤害的话,而诅咒仍是以承认此种魔力为前提的。
现代小说在本质上是反浪漫主义的,这种“深刻的反浪漫主义”——如同昆德拉在谈到卡夫卡时所推测的——很可能来自对性的眼光的变化。昆德拉赞扬卡夫卡(还有乔伊斯)使性从浪漫激情的迷雾中走出,还原成了每个人平常和基本的生活现实。作为对照,他嘲笑劳伦斯把性抒情化,用鄙夷的口气称他为“交欢的福音传教士”。
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并不直接讴歌性,在他们看来,性必须表现为情感的形态才能成为价值。在劳伦斯那里,性本身就是价值,是对抗病态的现代文明的唯一健康力量。对于卡夫卡以及昆德拉本人来说,性和爱情都不再是价值。这里的确发生着看性的眼光的重大变化,而如果杜绝了对性的抒情眼光,影响必是深远的,那差不多是消解了一切浪漫主义的原动力。
抒情化是一种赋予意义的倾向。如果彻底排除掉抒情化,性以及人的全部生命行为便只成了生物行为,暴露了其可怕的无意义性。甚至劳伦斯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无意义性,他的查太莱夫人一边和守猎人做爱,一边冷眼旁观,觉得这个男人的臀部的冲撞多么可笑。上帝造了有理智的人,同时又迫使他做这种可笑的姿势,未免太恶作剧。但守猎人的雄风终于征服了查太莱夫人的冷静,把她脱胎成了一个妇人,使她发现了性行为本身的美。性曾因爱情获得意义,现代人普遍不相信爱情,在此情形下怎样肯定性,这的确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性制造美感又破坏美感,使人亢奋又使人厌恶,尽管无意义却丝毫不减其异常的威力,这是性与存在相关联的面貌。现代人在性的问题上的尴尬境遇乃是一个缩影,表明现代人在意义问题上的两难,一方面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的真相,甚至看穿了一切意义寻求的自欺性质,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安于意义的缺失。
对于上述难题,昆德拉的解决方法体现在这一命题中:任何无意义在意外中被揭示是喜剧的源泉。这是性的审美观的转折:性的抒情诗让位于性的喜剧,性被欣赏不再是因为美,而是因为可笑,自嘲取代两情相悦成了做爱时美感的源泉。在其小说作品中,昆德拉本人正是一个捕捉性的无意义性和喜剧性的高手。不过,我确信,无论他还是卡夫卡,都没有彻底拒绝性的抒情性。例如他激赏的《城堡》第三章,卡夫卡描写K和弗丽达在酒馆地板上长时间地做爱,K觉得自己走进了一个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更远的奇异的国度,这种描写与劳伦斯式的抒情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区别仅在于比例,在劳伦斯是基本色调的东西,在卡夫卡只是整幅画面上的一小块亮彩。然而,这一小块亮彩已经足以说明,寻求意义乃是人的不可磨灭的本性。

现代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反对感情谎言。在感情问题上说谎,用夸张的言辞渲染爱和恨、欢乐和痛苦等等,这是浪漫主义的通病。现代小说并不否认感情的存在,但对感情持一种研究的而非颂扬的态度。
昆德拉说得好:艺术的价值同其唤起的感情的强度无关,后者可以无需艺术。兴奋本身不是价值,有的兴奋很平庸。感情洋溢者的心灵往往是既不敏感、也不丰富的,它动辄激动,感情如流水,来得容易也去得快,永远酿不出一杯醇酒。感情的浮夸必然表现为修辞的浮夸,企图用华美的词句掩盖思想的平庸,用激情的语言弥补感觉的贫乏。
不过,我不想过于谴责浪漫主义,只要它是真的。真诚的浪漫主义者——例如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患的是青春期夸张病,他们不自觉地夸大感情,但并不故意伪造感情。在今天,真浪漫主义已经近于绝迹了,流行的是伪浪漫主义,煽情是它的美学,媚俗是它的道德,其特征是批量生产和推销虚假感情,通过传媒操纵大众的感情消费,目的是获取纯粹商业上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