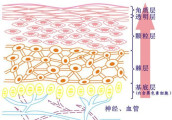【世界黑夜降临】
忘了在哪里看过一段话,大意是,为数不少的人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段或者瞬间,都产生过极端的念头。
我有过这种念头,是在某一年的春天。
这种念头的出现多少有些奇怪。虽然生活中发生了一些不太开心的小事,但总体上来说仍然风平浪静,所以我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这些负面情绪是什么时候悄悄地堆积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一开始是压抑,后来长时间的胸口钝痛,食欲跑到了九霄云外。
如果真的有心情坐标轴这种东西,那么每天的心情一定在零轴之下。我不清楚别人抑郁时是什么心情,只感觉自己像一具行尸走肉,所有的感官弱化到极致。
虽不曾失眠,但只想无休止地睡过去,每天一睁眼就是沉重的无奈和负累。
在我佯装镇定和平静的伪装下,身边的所有人大概都以为一切如常。
只有一个朋友有次面带疑惑地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了。”当我有点哽咽地说出“有时会想,从楼上跳下去就可以解脱了吧”这句话的时候,不止他被吓了一跳,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是的,那时我住在19楼,站在阳台、楼道或者电梯外的窗户前往下看,车辆紧张地挤在规划不太合理的道路上。
春天来了,一冬累积的雾霾正慢慢地让位给勉强晴朗起来的天空。
很多时候,我看着遥远的地面,和距离我仿佛十万八千里的欢声笑语,“从这里跳下去肯定活不成了"的念头便蹦了出来。冷风一吹打个寒战,我清醒过来,又瑟缩着退后几步。
我当然没有赴死的勇气,但我记得所有难以呼吸的瞬间,它们日日夜夜缠绕着我,比醒不过来的噩梦还漫长无边。
那段时间,我做了一些有点愚蠢的事情,比如将写了很久的日记本远远地丢了,社交网络上留下的消极言论也尽数删除。
还看了不少以前不太敢看的惊悚电影,用那维持不了几秒的心跳加速声验证一种存在或者活着的感觉,证实自己并非行尸走肉。
我也第一次在图书馆的小角落里发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书,比如塔罗牌算命,比如神秘的星象与命运。我意图找到一种说法来解释我的情绪异常只是短暂的波动。可惜并没有。
那是记忆里最漫长的一个春天。强烈的阳光照地灰尘的颗粒都清晰可见,可我什么光都看不见。那种感觉,有点像黑格尔所说的“世界黑夜”。
在好像我永远也无法逃脱的黑暗里,我想到最多的是他们。

【少年永远16岁】
因为上学早一点,十五岁那年的九月我开始读高三,我最喜欢的朋友刚过完十六岁的生日。九月是个多么好的季节,暑气退却,云层高耸,骑车在行道树中穿过只看到树影中明晃晃的亮眼光斑。
就是在那样的一天深夜,他在漆黑的山脚下吞下安眠药,永远地停在了十六岁。
隔天上晨读,一切风景和人事都照旧。旁边有人在背《将进酒》,也有人在背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一整个热闹的校园和平时并无差别。
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岿然站在门口喊我出去,我不明就里地看着她通红的眼睛,出去前还吩咐同桌帮我把数学作业交上。
在学校小花园的长廊下,她哭着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别难过。”
我猜不出是什么事情,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最大的事儿不过是月考考砸而已。所以尽管忐忑不安,我还是看到清晨的太阳光将她额间的碎发照成暖融融的黄色。
可岿然说:“他没有了。”“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我认识他五年,从初一到高三。自十岁开始我们便在隔壁班上课,在同一个考场里考试,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作为课代表无数次擦肩而过。
就在他离开的那个傍晚,我们还在食堂碰见,他微微地低下头,算作招呼。我没想到,那是最后一面。那个平日里最熟悉不过的笑容,竟成永别。
在那之前,我多少知道他有些自闭和抑郁,但即使让我做最狂妄的设想,也没想过他会走到那一步。
再说,最应该度过闪闪发亮一生的人就是他。他温和谦虚,像中古世纪的王子一样英俊。他每天从走廊上走过的身影都带着明润的光环。他在班里略微不好意思地唱《断了的弦》。
他戴着耳机听周杰伦的歌,看到我之后摘下耳机说:“我最喜欢他了”。他站在黄昏的小操场里微微地笑着。只让我想起歌词“夕阳下我向你眺望,你带着流水的悲伤”。他几乎承载了我对一个男生“美好”的全部向往与印象。
可是吧嗒一声,他如此轻而易举地像肥皂泡一样消失。
就是在那个秋天,我懂了《挪威的森林》里,渡边写给直子的话:“自你走之后,秋意也日渐加深。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心中仿佛出现了大洞般的感觉,是因为你的离开,还是因为时令更迭所致”。
又过了一年的秋天,周杰伦出了新专辑《稻香》,他唱“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又唱:“多少人在为生命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了。他也不知道另一个好友在日记里写,世界这么好,你怎么舍得离开。在那么多人的怀念、那么多人的不舍背后,我们没说出口的话都是,“多么希望你还活着啊”。
也是在那一年,外婆因为癌症去世。生前因为化疗受尽苦楚,瘦弱不堪,连喝水都艰难似受刑,但她还是握着我的手一字一句地问我,暑假快结束了吧?什么时候开学?我没回答,背过脸去泪流满面。
有那么多人迫切地想活下去,也有人那么轻易地就放弃了年轻的生命。但我理解他做出的决绝选择,和外婆最后的无限眷恋。
原谅我即使有无数次冲动的念头,但仍没去试着思索生死的要义。
只是在我最艰涩与绝望的时候,他的决绝与她的眷恋都告诉我,要活着。要活着。

【神啊,我自深渊里向你呐喊】
那个在世界黑夜里勉强生活的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重读《海边的卡夫卡》,看到了村上春树写的这段话:
“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
这是因为,沙尘暴不是来自远处什么地方的两不相关的什么。就是说,那家伙是你本身,是你本身中的什么。
所以你能做的,不外乎乖乖地径直跨入那片沙尘暴之中,紧紧捂住眼睛耳朵以免沙尘进入,一步一步从中穿过。那里面大概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唯有碎骨一样细细白白的沙尘在高空盘旋——就想象那样的沙尘暴。”
原来,我是“走在沙漠里的人”。
沙漠比沙尘暴还要空旷无边,但我得走出去。在新的日记本上,我这样写着。
要走过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方向,没有时间的沙漠。我得活着,不是苟延残喘、行尸走肉地活着,我得重新活过来,像所有的正常人一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救自己,但常常逃掉周五的课,周四晚上启身前往一场旅行。
看了附近好几座城市的大海,晴天里,小雨中,冷冷的清晨,迟疑的傍晚,海的模样并不一样,有时温柔,有时则带着汹涌的气势。
有一次天降暴雨,我打着摇摇晃晃的伞,看着海浪翻滚着朝我扑来,任凭冰冷的雨水将头发淋湿。它的开阔多少让我忘记了些什么。
我甚至差一点就投身一门宗教。电影《第六感》里说,在很久以前的欧洲,人们会躲进教堂里寻求庇佑。
郁郁寡欢的男孩将瘦弱的身体藏在教堂宽大的椅背后,将耶稣的小瓷像布置成一个佛龛一样的空间,用拉丁语念着“神啊,我自深渊里向你呐喊。”
虽然自始至终无法相信上帝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我每周天上午会坐很长时间的公车去城市对角线另一端的古老教堂,它斑裂的墙壁像老人的皱纹一样,让人很容易感觉松懈、妥帖和依赖。
作礼拜的人也多是老奶奶。我和她们一起,闭眼埋首,念很长的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们的,直到永远,阿门。”不知为何,这简短的几句话给了我奇妙的安宁。
有时一起读《约伯记》。
上帝要考验约伯的赤诚,于是夺去他的妻儿、家仆、牲畜、家产以及一切,只剩一个仆人踉跄归来:“唯有我一人逃脱,特来报信给你。”
匍匐在一无所有的苍茫大地上,他苦苦叩问:我已虔诚至此,何必要将如此苦难施与我身?我在日记本上一遍一遍地写那句可以作为答语的话,它说:“我们至轻至暂的苦楚,是为成就我们极重以致无比永远的荣耀。”
其他的时候,也去图书馆找了很多不知道能不能算作心理学的书去看,虽然它们未必专业和有用。
为了让自己开心,我开始每晚睡前在日记上列下生活里美好的瞬间,直到那个列表越来越长。每天拍一张照片,洗出来挂在书桌上,看着它们越来越丰富和多彩。
就在这样与自我对抗的日日夜夜中,我隐隐约约地看到黑夜的幕布拉开了一角,有光透了进来,仿佛所有的呐喊都得到了救赎。

【除了爱,一切都是妄言】
初夏要来的时候,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即将毕业、年仅25岁的女研究生从另一栋宿舍楼上纵身跃下,仓惶离世。
事情发生时我在家,回去之后风声渐平,熙熙攘攘的谈论早已冷却,我只听说就连她的父母男友都没觉察出任何惊天动地足以颠覆她生活的大事。
这在任何一个高校都不是新鲜的事情,可习惯带来漠视,漠视只能造就更多的悲剧。
朋友的父亲是心理医生,也是一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每年都有接连不断的学生和老师被送去他那里就医,有的救得了,有的救不了,多少年轻的身影和明朗的笑意,最后空余一声叹息。
但我长久地看着那片我们走过无数遍的水泥地面,想象她在窗口必定经过了无数的挣扎,才决定从淤积的情绪中解脱。
那是我第一次为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流下眼泪。也许我们曾在同一个教室学习,在同一个食堂里无数次错肩。
我们本该在相似的痛苦中结成同盟,握着彼此的手一起穿越黑暗,不让沙漠夺走宝贵的血肉之躯。
热泪过后,我只感觉她带去了我身体里最沉重的一部分,而光更多地透进来,黑夜正一点点地落幕。
后来,大概是六月底的一个清晨,那天有一门期末考试,我汗流浃背地醒来,另外几位姑娘在闹铃大作声中一边抱怨着天热一边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
明晃晃的太阳光照在我头顶的一角窗帘上。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呆了几秒,我察觉到,原来是久违的平静重新回来了。
胸腔里的钝痛消失地了无痕迹,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快乐混杂其中。一切熟知的世俗事物都散发着新鲜的味道。
我知道,我从沙漠里出来了。
再后来我就彻底好了起来,像从前一样活蹦乱跳,大嗓门和冷笑话甚至变本加厉地回来了。说很多话,唱跑调的歌,大声地笑,又恢复了所有朋友眼中开心果的模样。
但我知道在生活波澜不惊的外表之下有一些内容悄无声新地变了,身体和灵魂的内核分割破碎,然后重新粘合。
我之前笃信的一切至为重要的东西——高学历、好学校、以后的工作薪资、他人的肯定赞誉从此变得又轻又薄,那些拧巴和顽固的过去也一点一点地被捋顺。
我仍然需要工作谋生需要人情交际,但我第一次觉得生活它最迷人之处不过是妈妈一个温暖的拥抱、老友字迹翩然而至的明信片,甚至在正午拥挤燥热的公交车上喝一杯冰可乐的酣畅淋漓。
原来,最好的事情竟然是活着。

【我们一起好好活着】
《文学回忆录》里,木心说,贝多芬的每一个乐章,都在告诉人们,爱这个世界吧。
这也是我从沙漠里走出后时时刻刻想说的话。
若一定要将这段经历定义到成长的收获,那便是——不心心念念于过去,不汲汲营营于未知。
在那之后,我越来越能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美意。当人将欲求降至最低时,所收获的一切平凡竟都带着异样的惊喜。而那些曾百般束缚我的,“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
这段时间以来,我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回复与问询,也许被大多数人关注的“正能量”只是表层。那些文字的内核,其实是爱,就像我写给妈妈的——“除了爱,一切都是妄言”。
如果这些文字治愈了如此之多素未谋面的你们,大抵也是因为它们首先治愈了我。
因为只有我知道,这些一点一滴的“正能量”皆来自于我孤身一人在沙漠里举步维艰的前行,来自于干渴中的挣扎和窗户前的后退,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劝慰与说服,来自于我对——自己仍然活着,并且平安健康——的感激,这感激至死不渝。
若你也曾走出过沙漠,我知道你模糊的笑容背后一定有些东西坚不可摧,也确信今后你心底定然路途坦荡。
若你从未走过沙漠,我愿你永远都不要走。因为这个世界它的月朗星沉,它的情真意切,原本就值得深爱啊。
剩下的,我们一起好好活着。
不辜负这一场潋滟春光,和这一路山高水长。
后 记
写这篇文章时看到了两条新闻,一条是“历史系研究生因不堪毕业论文和就业压力自杀”,另一条是“某报副总编自杀离世,因工作压力大”。
这样的消息听来便是沉痛。如果文字能有力量,尽管任何关于生死的谈论都是虚妄,但我还是想说,活着吧,活着试试,试试会不会有好的事情发生。
多么希望你一直快乐,并有笑容。